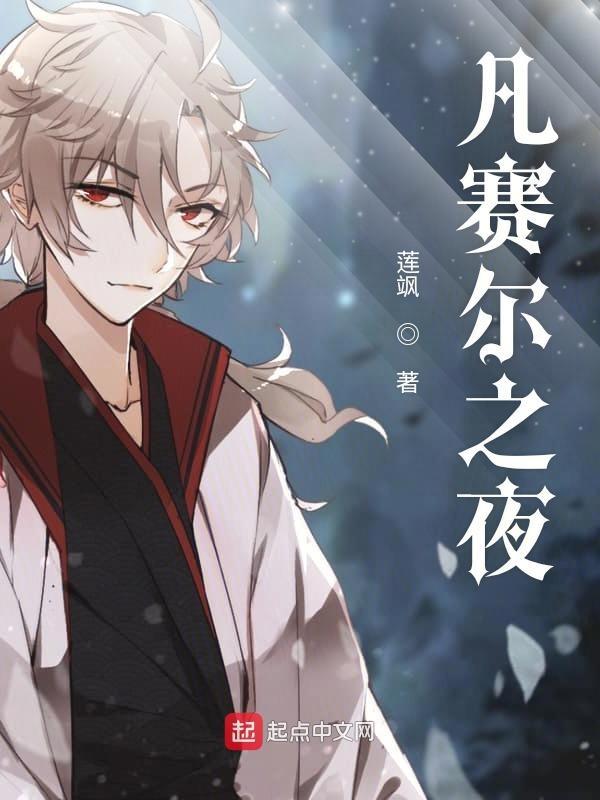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但押对储君晋江 > 第15节(第1页)
第15节(第1页)
见擦不掉,他叹气,“可惜了。”
林惊雨低头,“抱歉。”
她忽然见案子上放着镯子碎玉,用帕子乘着。
林惊雨心虚伸手要拿回,手腕却被白净有力的手指握住。
“可惜了,这么好的镯子,到了林二小姐的手中还没两个时辰就碎了,林二小姐就不解释一下?”
林惊雨扯了扯手,扯不回。
她今日心情极差,加之脑袋发晕,没好气道:“反正不是臣女摔的,殿下怪摔镯子的人去。”
她又嗤笑一声,“忘了,在殿下的眼里,什么都是臣女的错,臣女自私,臣女撒谎成性,臣女是个坏女人。”
她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。
“凭什么你们男人可以为权利虚与委蛇,争个你死我活,我们女人就不行,使个手段,就是心机,有野心就是贪图荣华,都是为自己罢了,分什么高低贵贱。”
萧沂望着她的眼泪一顿,分明是哭着的,双眼却是倔强之色,像是在强忍眼泪,却又憋不住。
比起从前那副娇滴滴的可怜样子,此刻蛮不讲理的狼狈模样更是真实。
萧沂缓缓松开手,“林二小姐怪错了人,我可没有这么说过。”
“是,你没有说过,但殿下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,处处提防我接近太子,看我像是看一条蛇。”
难道不是吗,萧沂心中想着,但形容一个姑娘是蛇不太恰当。
况且,实话说她生得要比蛇好看。
萧沂漫不经心抿了口茶,“顶多,是朵危险的花罢了,我只是怕,我那皇兄承受不住。”
“殿下谬赞,臣女又不是食人花,还会吃人不成。”
萧沂认同地颔首,“吃不吃人,还真说不定。”
林惊雨抱膝,探着脖子瞪了他一眼,“总比殿下这条咬人的狗好,见了我就乱咬。”
萧沂蹙眉,觉得今日她有些伶牙俐齿,咄咄逼人。
不过,还是一样爱哭。
像个孩子,于是乎,他不想与一个孩子计较。
“跟家里吵架了?”
林惊雨撇过头去,“殿下还要管臣女的家事不成,殿下是不是还要给我安个忤逆父母之罪。”
萧沂倒觉得比起他,此刻她更像一条疯狗。
他不恼,平静道:“这关乎到我该把你送哪去,万一林二姑娘是离家出走,我总不能忤逆了林二姑娘的意愿。”
“旁的人都是贴心地把姑娘送回去,殿下倒好。”
萧沂一笑,“本殿不想自讨无趣。”
“若是真能离开那个家就好了。”
林惊雨抱膝,哽咽道:“那里,从祖母离世后,便再无我的容身之地,父亲不管,大夫人处处刁难,亲娘根本也不亲,连府里的下人都欺负我,我不喜欢那个地方。”
萧沂握着的茶一顿,他曾让手下查过林惊雨,手下一一禀报,到最后,道了声她过得很凄苦。
他问,“除了齐旭,除了皇兄,为何不是别人。”
林惊雨不明所以,“我先前不是说过了么,我想做皇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