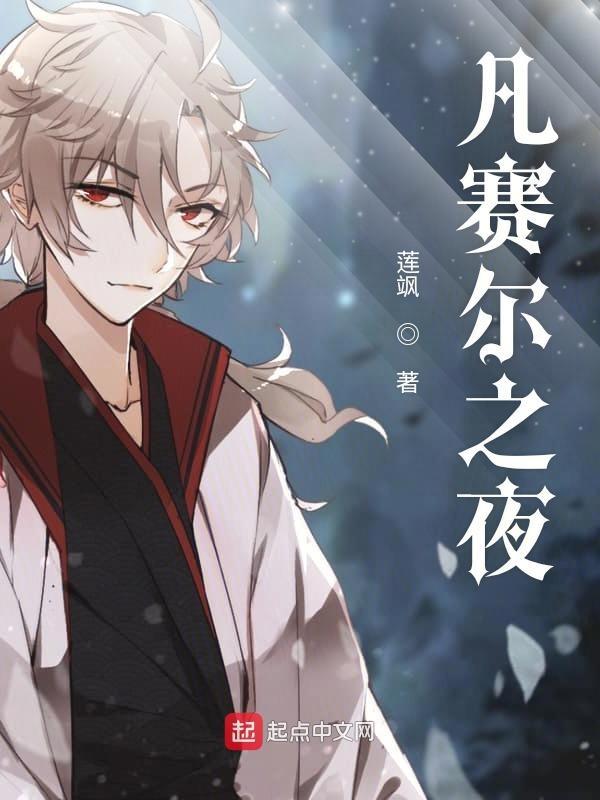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大理寺断案实录 三七之间 > 第3章(第1页)
第3章(第1页)
桑榆仅仅一瞥就看出事情有异,那人身上的伤痕不像是出于他人之手。
桑榆口齿清晰,言辞犀利,三两下道明伤口为何所伤,又如何击打至此,那人被问的满天大汗,不知所云,张明府见状拉回去敲打一番,那人终于承认伤痕是为了嫁祸他人,自己殴打而来。
桑榆一战成名,此后一段时间张明府几次招她相助,每次桑榆都能看出些许破绽,破案效率之快,准确性之高,让饱受破案之烦恼的张明府喜笑颜开,心情都愉悦上不少。
作为不良帅,他自然也亲自见识过,并且尤其喜爱,总觉得每次听她分析案子都颇为赏心。
桑榆可不知道这些,她回到板车旁,掀开板车上的白布,露出里面脸色青白,气息全无的柳大郎。
是的,板车上正是柳大郎的尸身,柳大郎是来长安求学的外乡人,现在住的地方是一个好友租借的,他一死却不好一直放在房子里,不良帅一琢磨反正都是要带回衙门送到义庄的,索性借了板车一并拉着。
这就苦了一群跟着的学子了,柳大郎已经死去多时了,尸身开始微微发臭,之前有白布蒙着还好,现在白布一掀开,那股味儿略微靠近都叫人难以忍受。
桑榆无视周围人异样的眼光,从容地掏出布巾遮住面部,也不碰尸体,只是细细瞧看一番。
不良帅也不阻止她,随她看。
柳大郎身上的衣服是长安学子常穿的青色长袍,上面满是污渍,颜色也有深有浅,靠近了还能闻到些许刺鼻的味道,她掏出手帕,将衣服上的污渍一一捏起,就连腰带也不放过。
此时身处闹市,验尸什么的肯定是不可能了,桑榆也不在意,隔着手帕在柳大郎的肚子上按了按。
都说柳大郎贪吃,爱喝酒,身材胖乎,尤其是肚子上的肉,躺在板车上像是怀孕的妇人一般,桑小榆这么一按,整个肚子凹出一个坑,像是按在了一团软絮上。
只是这就苦了板车旁的衙役,桑榆这么一按,柳大郎的口鼻,身下都吐出恶臭,酸腐的味道折磨着他们的嗅觉。
衙役们纷纷捂住口鼻后退,就连原本打算上前观望的不良帅都止住了脚步。
他蒲扇似得大掌在面前挥舞几下,黑俊俊的脸上满是嫌弃,“小娘子,不如咱们将人拉回衙门义庄再验如何?”
桑小娘子乖巧可怜,何必做这样的肮脏事?还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。
桑榆闻言笑笑,抬起手,将帕子包起来,随口问道:“昨天你们一直在一起吗?吃食都一样?”
仇二郎道:“当然,昨天晚上我们是在西市的秦家酒肆吃酒。”
一直沉默的沈四郎也点点头:“正是,我们每隔几日都小聚一下,也算是秦家酒肆的常客了。”
桑榆继续问:“那你们结束之后还去别处了吗?可吃些什么?”
“没有。”沈四郎肯定道:“我们结束之时都有些醉意,暮鼓已经敲响,掌柜还特意提醒我们注意时辰,我们这才各自叫车回家。”
:点心
说完叫来小厮,“因张大郎是独自前来,所以还是我的小厮驾车送他归家的。”
实际上是因为张大郎家里没有仆从小厮,沈四郎身体不好酒吃的少些,这才能照顾一二。
那小厮唯唯诺诺点头,表示除了张大郎之外还送了其他两个学子归家,其中就有柳大郎,柳大郎到家已经很晚了,是最后一个送回去的,他将人交给照顾柳大郎的婆子之后就驾车离开了,最后差点赶上宵禁。
桑榆点头,柳大郎身上都是酒味和呕吐异味,可见当时吃了不少酒。
张大郎喊道:“即是如此,柳大郎归家之时还活着,如何能肯定是我下毒?”
仇二郎闻言道:“不是我等要怀疑你,只是我们吃酒时只有你有下毒的时间。”
据仇二郎等人回忆,当时他们在二楼的包间里吃酒作乐,忽闻楼下传来叫好声,原是因为有游学才子新作了一篇诗词,引的在场的文人雅士纷纷叫好。
本朝文风盛行,世人对文人极为推崇,若遇上好的文章诗词,少不得要鉴赏一番,再与那文人相交一二。
当下他们都下楼准备结交,只有张大郎以身体不适为由独自留下。
仇二郎僵着一张脸,一双眼睛满是血丝,他斥道:“什么身体不适,全是妄言!张大郎在药铺做事,熟知药理,平日与柳大郎多生口角,想加害于他有的是缘由。”
张大郎张张嘴,想要辩解,发现有口无理,他早前因为记错账被掌柜的说教一番,本就心情抑郁,又想到自己读书多年却一事无成,现在全靠阿耶和周氏做买卖营生养家。
昨天那文人的好文章让他心下更加烦躁,才借口身体不适留下独自吃酒。
可是,这话他说不出来,他的同窗好友,父亲妻子都在这里,他如何能说出此等丧气之词。
不良帅看到张大郎颓然的样子,只当他是已经认罪了,当下笑着对桑榆道:“桑小娘子果然聪慧过人,只消两句便叫凶手服气。”
桑榆当然知道他是在恭维自己,她只不过是随口问了几句,那有他说的那么好听,虽然这话听着很舒服,但是也听出些许轻视之意。
少年人啊,果然还是太年轻。
她也不废话,直接问那小厮,“你家郎君和柳大郎是一起去酒肆的吗?”
小厮呆了一下,回道:“是的,因柳大郎来长安求学,平日里过的比较清俭,我家阿郎与他交好,平日里会常邀他同行,这次也是特意来接他,半途又遇到仇二郎君,三人一起去的酒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