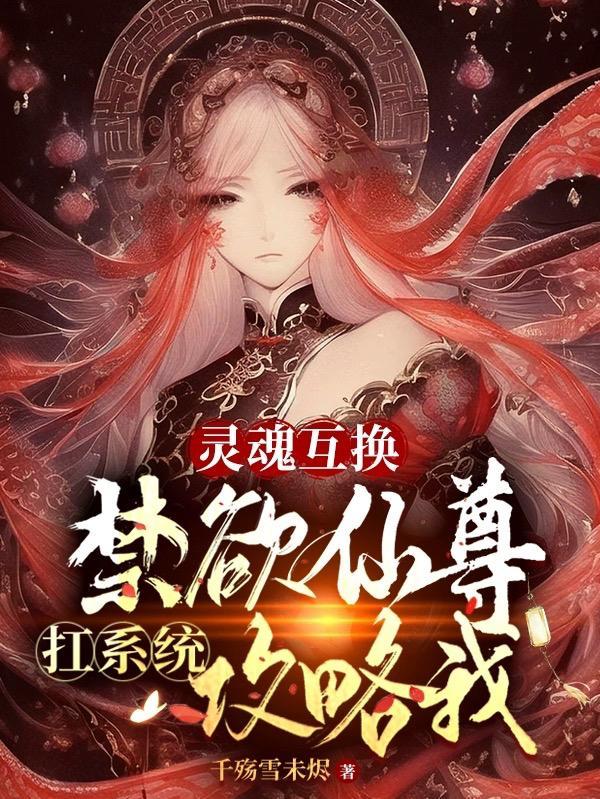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捡了个疯女人 > 第61章(第2页)
第61章(第2页)
呜呜呜。
一阵虚弱的鸣叫叫停了抬腿准备离开的人。
扒开那簇草,她在最里面找到了源头。
一只白色的生物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,原先柔顺的白毛变得灰扑扑的,有些还打起了缕。
“你还好吗?”小潞蹲在地上问。
“不太好。”
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然后小潞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“……”
真走了?那你问什么?
就在它昏昏欲睡的时候,嘴里被塞了一种冰凉的东西。下意识咽下,它惊恐地睁大了眼。
原先走掉的人去而复返。
“你现在还好吗?”
“还好。”
然后小潞又走了。
“……”
没懂。
被人从天上踹下来的滋味可不好受,阿肆一轱辘躺了回去,睡了个安稳觉。
隔日,小潞又来了,带了两条烤鱼。
“吃吧。”她把东西一股脑丢在地上。
没和她客气,阿肆梗直了脑袋,狼吞虎咽。
吃饱喝足后,它开始和旁边小口小口撕着鱼肉的人攀谈。
“你哪来的鱼?”这附近也没有河啊。
“拿了别人的。”
“?”
“她们三个常常和我玩,不会在乎这些。”想到了平日里谢瑜三人的行径,大不了就是受伤罢了,玩耍受伤总是难免的。
虽然她们和自己玩的时候老是说些自己听不懂的话。
她长这么大从未有人教导过她什么,但她经常看见密林中有还未足月的小兽纠缠在一起互相逐咬。
反正阿肆也不能动弹,小潞曲着腿坐在它旁边,权当它是个异变的树洞。
“但是我最近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。”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僵硬地扯起了一抹弯起的弧度,“她说这叫笑,开心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表情。”
可是她在此之前从未见过,没在动物身上见过,也没在人身上见过。
“那你喜欢和她呆在一起吗?”阿肆毛茸茸的脸下是皱起的苦笑。
“不知道。”
但她想自己也没那么喜欢之前的那种玩法。
在密林里休养生息了几天,小潞该离开了。
途中偶遇一片花海,她矗立思忖,最后摘下了里面最鲜艳的那朵,小心翼翼地塞进怀里。
手中执笔,撑着脸百无聊赖地在书上写画了几笔,谢韵不耐烦地丢了出去,“凭什么那种贱人都有人护着!”
旁边的两人殷勤的献计,“给苏澜点小苦头吃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