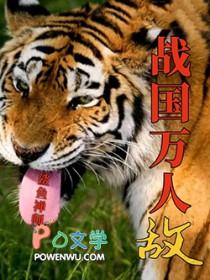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娇宠小太后 小舟遥遥 > 第295章(第1页)
第295章(第1页)
云绾浑身发软地坐在榻边,半边身子勉力撑着案几,她试图将脑中那种天旋地转的晕眩感压下,可她越是想压下,耳边的嗡嗡响声越发清晰响亮,叫她额心涨痛,突突直跳。
“娘娘,您喝点水。”玉竹提壶倒了杯温水,双手捧给云绾。
云绾单手撑着额头,另一只手接过茶杯,手指还抖得厉害,哆哆嗦嗦间不少温水洒落在桌案上。
不行,她得冷静,冷静下来。
深吸一口气,她将那剩下的半杯水一饮而尽,可不知为何,明明是无色无味的水,她喝到嘴里却泛着一股酸味。
那味道叫她恶心作呕,放下茶杯,单手按在胸口,侧身就要呕吐。
“娘娘!”玉竹刚弯腰将那本军报拾起,就见自家主子干呕起来,霎时吓得一跳,忙喊道:“来人啊,快去请御医!”
“没…没事……”
细白手指紧紧捏着桌角,云绾强打起精神,止住玉竹:“不用叫御医,我没事。”
“可是,娘娘您的脸色很差……”玉竹看着那张失了血色的娇美脸庞,担心得两道眉毛都紧紧揪在一起:“不然奴婢还是叫御医来瞧瞧吧。”
云绾摇了摇头,余光落在那封军报上,心绪沉重。
皇帝下落不明已足够叫人惶恐,若是这个时候,她还找来御医,指不定外面要怎么传言。
“我没事。”云绾语气坚定,又吩咐着玉竹:“你去将阿隼找回来,伺候我梳妆,我要去趟紫宸宫。”
玉竹见她坚持,只好领命下去。
云绾偏过头,视线再度落在那本军报上,指尖颤抖地拿起,“下落不明”四个字再次撞入眼帘,犹如无数银针细细密密地扎进心口,一点点的疼痛汇聚凝结,那份痛意越来越深,叫她呼吸都变得艰难,胸口闷得厉害。
“呕——”她反手按住军报,再度俯身干呕起来。
周围宫人吓了一跳,急急忙忙上前递水递帕子。
云绾有气无力靠在软枕之上,面色苍白地想,怎么就下落不明了呢?
不过一个小小淮南之地,他带着一万精兵,攻打下来应当不成问题的啊。
难道是他急着赶回来,冒进疏忽,因此中了敌人的算计?
若真是因为这个……
云绾双眼一阵发黑,老天为何要这般戏弄她,若司马濯真是因此而有何不测,那她余生岂不是要背负着愧疚度日,良心何安?
她脑袋混沌地换了衣衫,没多久,玉簪也将阿隼找来回来。
小家伙本来老老实实按照司马濯的吩咐,每日扎半个时辰的马步,这时间还没到呢,就被母亲急急寻了回来。
此刻他一张小脸还通红着挂了汗,见到一袭较为庄重礼服的阿娘,不由愣了一愣:“阿娘,您这是要出门么?”
云绾看着这张酷似司马濯的小脸,眼眶不由泛酸,轻点了下头:“是。”
她紧紧掐着手指,尽量克制着自己胸膛翻腾的情绪,柔声与阿隼道:“你快进去洗把脸,换身干净衣裳,与我同去紫宸宫。”
阿隼心头好奇,紫宸宫不是爹爹的宫殿么?可现在爹爹都不在长安啊,他们过去做什么?
不过他向来对他娘的话言听计从,也没多问,便乖乖随着玉簪去洗脸换衣了。
半个时辰后,凤辇在紫宸宫稳稳落下。
听到贵妃牵着小殿下来了,李宝德急忙扶着帽子赶来迎接:“奴才拜见娘娘,拜见小殿下。”
云绾深深看他一眼,牵着阿隼的脚步不停,一边往里走一边交代着李宝德:“你拿着本宫的懿旨,将宰相杨硕、户部侍郎陈谦、禁军统领卓鹏正以及兵部尚书王鹤请进宫来。”
稍顿,想到这军报是一式两份,一份直达中枢,一份直接到她手中,她既收到了,想来那几位股肱重臣也都拿到了。
她沉声道:“他们此刻应当都在中书省,正好一齐叫来。”
李宝德听闻这吩咐,也意识到出了大事,面色紧张地看向云绾:“娘娘,恕奴才多嘴,这…这到底是出了何事?”
云绾看了眼李宝德,知道这太监从始至终对司马濯都是忠心耿耿,万一司马濯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,日后她与阿隼还有不少事须得他来协助,便从袖中将那封军报拿出,递给了李宝德。
李宝德双手接过,当看到白纸黑字寥寥数语,霎时倒吸一口凉气:“这…这……”
云绾朝他摇了摇头,示意阿隼还在。
李宝德立刻闭上嘴,憋了好一会儿才平稳情绪,垂首道:“娘娘,您和殿下先在里头歇息,奴才这就去请诸位大人前来议事。”
云绾嗯了一声,牵着阿隼,轻车熟路地往殿内走去。
阿隼极其敏锐,也意识到出了大事,他看着自家阿娘凝重的侧脸,很是体贴得没有追问,而是乖巧地依偎到她的怀里:“阿娘,你抱抱我吧。”
云绾微怔,对上儿子那双水洗葡萄般的晶莹黑眸,忽的意识到什么,心头绵软地将孩子搂在怀中。
他知道,她此刻需要一个倚靠。
哪怕他还小,他也想给她一份力所能及的安慰。
“阿隼……”云绾搂着他,喃喃道:“还好,还有你在。”
阿隼悄悄握紧了小拳头,他懵懂意识到,爹爹或许失约了。
不多时,以宰相为首的几位重臣都来到紫宸宫。
云绾坐在珠帘之后,阿隼听她的叮嘱,小脚并拢,肩背挺直,端端正正坐在榻前。
阿娘说了,他是皇帝唯一的儿子,是国朝未来的储君,就该有天之骄子、皇室血脉的气势与风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