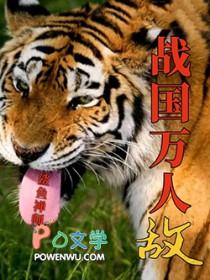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夫君他不太对劲免费阅读 > 第31章(第2页)
第31章(第2页)
裴清川垂着手看着她们在前面说笑,周遭交谈声不绝,所有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和期待,他却像是什么都听不见一般。
只目光沉沉的看着闻昭。
写过信。
他同她曾经写过信?
是吗?
他怎么不知道。
第一次知道她,便是在祁州,怎么可能在此之前写过信?
大内的船舫行得快,不久便越过了袁家的,连带着吟唱的声音也逐渐消弭。
三人折身要回了里面,转身对上站在船头,脸色有些不好的裴清川。
袁令仪心下一惊:“表哥,真吃醉了?”
只半杯酒,不至于教他醉吧,去年冬至他还吃了整整一杯,那日脸色也没难看成如今这般。
“没有。”
良久,裴清川才出声。
半杯酒而已,且是菖蒲酒,他甚至都没喝完,怎会吃醉了。
但那句话清晰入耳,若非他吃醉了,又怎会听到这奇怪的事。
他的目光落在闻昭身上,没有错过她脸上的紧张与担忧。
他闭了闭眼,侧过身让路:“进来吧。”
几人重新坐定,袁嘉善双手撑在身子两侧,看着身侧的妻子,懒洋洋开口:“我过阵子就回了,正午太阳大,你们二嫂嫂禁不住晒。”
三人皆应下。
很快外面又热闹起来,袁二嫂嫂适才站的久了,这会儿说脚疼,没有出去。
袁令仪便拉着闻昭出去了,走了两步,见裴清川坐在那儿敛眸看着手里的酒杯,她又折回去将他给拉了起来。
笑着说:“还是别在此处碍二哥哥的眼了。”
裴清川由她拉出来,见闻昭笑吟吟的看着自己,他微颔首,站在她身侧。
河面起了风,吹起小娘子的裙摆,飘过来覆在他身上。
他收颌,垂眸看向身侧的人。
他从来都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性子,不可能任由疑惑存在心里,这不是他裴清川。
风声呼呼,他没再犹豫,问她:“我之前还同你在信中讲过什么。”
闻言,闻昭奇怪的看了他一眼,彼时的自己识字不多,须得娘亲一字一句的读与自己听,但他长于自己,那时也早已启蒙。
且后来有一回,他还寄了他抄写的《洛神赋》来,自己也曾临摹过他的字。
那信即是他亲手所写,又怎会忘记里面的内容。
风渐紧,她又嗅到他身上淡淡的酒味,便只是当他吃醉了酒,忘了旧事,温声回了一句。
“只说了几回京城过节的盛况,还有诸如繁楼和金明池这等富贵地的事。”
话音才落下,闻昭手腕忽然一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