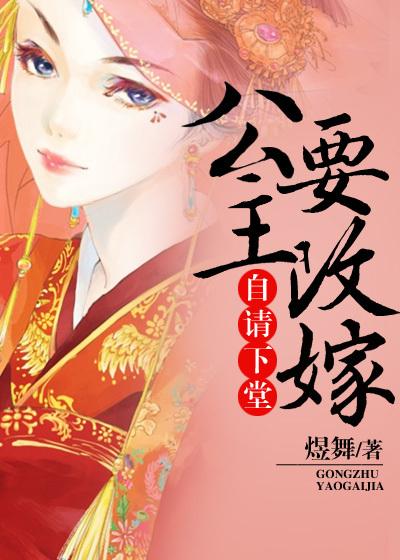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华夏事件追踪 > 第五十四集 太子回京(第2页)
第五十四集 太子回京(第2页)
便在此时,吐蕃国内发生政变,论钦陵伏诛。
当初赞普器弩悉弄即位之时尚幼,论钦陵兄弟用事,因皆有勇略,周边诸胡畏之。论钦陵于是居中秉政,命诸弟分握重兵分据方面,其中赞婆常居东部,为中国边患三十余年。
此后器弩悉弄逐渐长大成人,为夺权亲政,阴与大臣论岩密谋,欲尽除论钦陵兄弟。
万岁通天元年,论钦陵与弟赞婆大破王孝杰于素罗汗山,并私与武周议和,使器弩悉弄对其猜忌愈重。
适逢论钦陵出外,赞普便诈称外出会猎,召集禁卫亲兵,前往论钦陵驻地阿秦地区,擒执论钦陵在朝亲党二千余人杀之,复召命钦陵兄弟还朝。
未料消息走漏,论钦陵就此举兵,宣布自立,不再尊奉王命。赞普亲引军讨之,论钦陵部下不愿与赞普为敌,大都阵前倒戈,论钦陵最终兵溃自杀。
画外音:论钦陵乃吐蕃大相禄东赞次子,共有兄弟五人,长兄早亡,三弟分别为赞婆、悉多、勃论赞刃。三兄弟长期领兵屯戍边境,皆有才略。论钦陵为扩张国域,突袭占据吐谷浑故地,控制青海西部,名震西北,当世无二。唐蕃双方在青海农业区以西展开长期较量,钦陵不仅派弟赞婆长期镇守青海,且自己经常率兵活动于此,苦心经营半生。但争夺安西不果,要求唐朝撤出又被拒绝,终被郭元振离间之计所算,死于内讧夺权。
据敦煌藏文文献记载,论钦陵乃是常胜将军,平生未曾一败。先在大非川之战中一举打败唐朝战神薛仁贵五万大军,彻底控制吐谷浑国土,为吐蕃国势壮大,疆域扩张做出巨大贡献;后又接连打退李敬玄、王孝杰大军,保住吐蕃西南强国地位。
论钦陵不仅善于作战,而且能言善辩,极有远见卓识。
在素罗汗山大战之前,唐军统师王孝杰曾致书钦陵:吐蕃军旅如虎成群,又似牦牛列队,所计之数,吾亦相当。谚云:“量颅缝帽,量足缝靴。”我大军奋上国之威,犹如天降霹雳以击山岩,则岩石虽大,岂能当此雷霆之怒耶?
论钦陵览书笑道:我岂不知你只是一介武夫?又与我论甚譬喻,说甚谚语!
乃挥笔复书:我闻小鸟虽众,为一鹰隼之食;游鱼虽多,皆入一水獭之腹。麋鹿锐角虽多,岂能取胜?牛角虽钝且短,却足自卫。松生百年,一斧足伐;江河纵阔,一庹革舟可渡。青稞稻米长满坝上,却入于一盘水磨之中;星斗布满天空,一轮红日使之黯然失色。一星焰火,足焚高山深谷所有之木;一股泉水,源发山洪足漂坝上全部之林。虽满地土块,若使一石滚动,请观是其石破,亦或巨块粉碎?公之军旅实如湖上蝇群,为数虽多,不便指挥,便似山头云烟,对在下无足轻重也。吾之军丁虽少,岂不犹如一把镰刀,以割刈众草乎?牦牛虽大,以一箭之微射之,岂不能致死乎?
连篇累牍,类譬巧喻,妙语叠出。
论钦陵既已败亡,其弟赞婆在吐蕃立足不住,遂率其所部千余人退出青海东奔,到安西四镇,来降武周。
武皇太后在神都洛阳闻报大喜,遂命右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,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为接应大使,率领精骑前往边境迎之,诏封赞婆为特进、归德王。
其后论钦陵之子弓仁亦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,武皇复拜为左玉钤卫将军、酒泉郡公。
冬十月,论赞婆等到至东都,参拜武皇则天大帝。武则天宠赏甚厚,使将其众共守凉州洪源谷。赞婆不久病卒,诏赠特进,安西大都护。
久视元年秋,吐蕃大将麹莽布支率骑数万寇掠凉州,兵入洪源谷,将围昌松。
周将陇右诸军大使、西州都督唐休璟闻敌大至,不及调动大军,只引州中数千人御敌,两军遇于洪源谷。
因与众将临阵登高以望,见吐蕃军衣甲鲜盛,人欢马乍,部将皆有恐惧之色。
唐休璟知道众人有畏敌之心,反而大笑道:自论钦陵身死,赞婆归降我大周之后,吐蕃再无能战之将矣。今麹莽布支新领贼兵,不先练兵习战,反急欲曜武所威于我大周,故命其国中贵臣酋豪子弟,皆都从军。你等观其人马虽精,但皆不习军事,不足惧也。此实易与耳,不信便看吾为诸君取之!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乃被甲先登,与贼六战六克,当者披縻。
终大破敌军,斩其副将二人,获首二千五百级,筑京观而还。
唐休璟振旅还师,武则天亲迎于玄武门外,搞赏三军将士。适逢吐蕃赞普遣使前来请和,武皇因设宴款待来使,使唐休璟作陪。
吐蕃使节于席间屡次偷窥唐休璟,武则天问其缘故。蕃使奏道:洪源大战之时,便是此位将军,在战场上身先士卒,雄猛无比,杀我吐蕃将士甚众。今对面而坐,故欲求识之。
则天闻言大加叹异,对众臣道:一战便使敌人深记容貌,且怀敬畏,真将军也!
遂擢拜唐休璟为右武威、右金吾二卫大将军。
字幕:圣历二年,春二月壬辰日。
武皇太后以魏元忠为检校并州长史,充任天兵军大总管,北上以备突厥;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,仍充陇右诸军大使,专掌怀抚吐蕃降者。
是年八月,娄师德不幸卒于会州(今甘肃靖远)任上,时年七十岁。
武皇闻之大为悲悯,诏命舆尸返乡厚葬,追赠凉州都督,赠谥号曰贞。
此时武皇太后自觉春秋已高,担心身后太子与诸武不能相容,遂召太子李显、相王李旦、爱女太平公主,与武攸暨等诸侄及孙聚于一常,盟为誓文,许诺绝不相互残害;祭告天地于明堂,铭之铁券,藏于史馆。
是年秋七月,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,以代会稽王武攸望。
当时王及善为内史,因见张易之兄弟仗恃武皇宠溺,每侍内宴时无复人臣之礼,便屡屡上奏弹劾,以为不可如此,长久以往,必致惑乱朝纲。
太后大为不悦,乃诏复道:贤卿年高老迈,此后不宜更侍游宴,但检校阁中可也。
王及善因此称病,请假月余不出,武皇太后乐得耳根清静,也就不问。王及善上疏致仕,请乞骸骨还乡,太后却又不许。
其后未久,武皇复下诏命,以王及善为文昌左相,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,仍并同凤阁鸾台三品,并佐朝纲;鸾台侍郎、同平章事杨再思不称相职,罢为左台大夫;天官侍郎陆元方擢为鸾台侍郎、同平章事,相王李旦兼领检校安北大都护。
八月癸丑,突厥十姓中突骑施部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武皇,朝贡大周天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