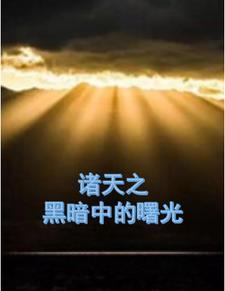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折娇姝韵 > 第26章 第 26 章 你也觉得荒唐对吗(第2页)
第26章 第 26 章 你也觉得荒唐对吗(第2页)
神龛中的观音面色平静而从容,仿佛能包容世间一切过错。在观音的注视下,皇兄朝她走来。
“瞒着你,是皇兄的错,皇兄向你道歉。但是——”
他话锋一转,沉声诘问:“让我猜猜,那日马球场看台上你与陆昭怄气,是不是因为他之前说过要向父皇求娶你,你却许久没收到任何消息?”
谢静姝面色苍白,张了张嘴想要辩驳却无话可说。因为事实确实如此。
谢檀弈嘴角冷冷一笑:“陆霆为保陆家安稳只会选择中立,所以他绝不会同意自己的儿子娶太子一母同胞的亲妹妹。如果不激陆昭一下,他也不会贸然向父皇求娶你。在陆昭心里,你远不如陆家重要。”
谢静姝面如死灰。
皇兄不知何时已经走到她身边,温热的掌心按在她的肩膀上,推着她往回走。
“瑛瑛,你在这段感情里陷得有些深了。一个男人而已,你不该为此失魂落魄。可以嘻戏,但切忌沉溺。”
“没有。”谢静姝倔强道,“我很清醒。”
“如果你很清醒的话,皇兄不会瞒你。”
谢檀弈按着她的肩膀令其坐上扶椅。弯腰捧着她半张脸,凝望着她的双眸,涩声道:“如今兄长在你心里的位置怕是比不上他。”
“怎麽会?皇兄是怕我会为了陆昭坏事吗?皇兄这样想我?”谢静姝立即反驳,抓住谢檀弈手腕,擡头望向那双深如潭水的眼眸,“皇兄若提前告知,我怎会不帮你?我是气你欺瞒。皇兄不拿瑛瑛当自己人。”
谢檀弈眸光闪出一丝惊喜,“哪怕令陆昭万劫不复你也会站在皇兄这边吗?”
听到这样的话,一口气堵在谢静姝胸口上不去也下不来。为什麽总要如此极端?非得你死我活才肯罢休?
握在谢檀弈腕上的手似脱了力般垂下,她亦低着头,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一段话,“陆昭有他的立场,我也有我的坚持。如果这次说好不让陆昭受这麽重的伤,我是站在皇兄这边的……”
“皇兄就是你的坚持?”
谢静姝抿着唇没回答,谢檀弈便当她默认了。
“一定是的。”谢檀弈抚摸着她的眼睑喃喃自语,显出一种病态的偏执。
“瑛瑛这些天没睡好觉,都有黑眼圈了。”
他在观察她,贪婪地将五官,甚至是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都纳入眼中。
谢静姝这才发现他们靠得很近,近得几乎能交换呼吸。
皇兄一只手撑着扶椅把手,另一只手描摹她的眉眼,俨然将她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。
可这样狭窄的范围并没有令她感到压迫,檀香环绕,反而有种莫名熟悉的安心。
她从小就喜欢待在皇兄身边,这意味着安全。
可如今,这种固有印象却在逐渐被打破。皇兄凝视她的眼神,着实有些晦涩难懂。
她没来由地开始紧张,喉咙发干发涩。想要逃离,可皇兄的目光又如潮水般将她卷回去,避不开,逃不掉。
这种未知的感受令她恐惧。
檀香又似酒香,她泡在里面,浑身发软,竟在这令她恐惧的温泉里慢慢沉溺。
“陆昭只不过是你未成婚的驸马,皇兄才是你唯一的亲人。”
这句话对,又没那麽对。谢静姝挑不出错处,尽管犹豫,但还是认可地点点头。
谢檀弈笑得温柔至极,轻轻地捏了捏她的耳垂说,“瑛瑛真乖。”
他靠过来,额头抵住她冰凉的额头。
谢静姝感到一阵温热。呼吸缠绕,鼻息交织,若是再贴得近一些,怕是连嘴唇都要碰上。
他们小时候总是这样玩,谁撑不住先笑谁就输了。
皇兄大部分时间是不笑的,通常是她先咯咯笑着认输。皇兄大她将近六岁,加上早慧,等她三四岁沉迷于玩额头贴额头的游戏时,皇兄已经是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小大人了。皇兄其实并不爱玩游戏,只是喜欢陪着她。
霎那间,谢静姝回想起许多往事,可越回想,越觉得如今的情况不对劲。
她说不出来哪里不对,只是奇怪,为什麽这次跟皇兄额头贴额头会感到没来由地慌张?为什麽她的喉咙会像发高烧一般红肿发痛?为什麽她会心虚到连手指都在微微颤抖?
——“你不觉得,跟太子这般当兄妹,有些过于亲密了吗?”
她想起陆昭的话。
额头贴额头算是亲密吗?也许是吧。
可这是她哥哥,唯一的亲人,就算那件传言为真,他们也是早已被认定的亲人。亲人间亲密是天经地义的。
——“妙仪妹妹也不小了,还成天跟在兄长身後形影不离。兄妹间如此亲密,你日後的夫君难免吃味呀。”
她又想起谢绍舟在中秋晚宴上说的话。那时听还不觉得刺耳,如今回想起来竟觉得如鲠在喉。气得十指用力扣住扶手。
放屁!她跟皇兄清清白白,岂容你一个外人置喙?
温热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,痒,令她不禁想躲。可谢檀弈的手却缓缓下移,按住她的後颈,安抚性地按摩。
恍惚间,封印记忆的尘土像是被风吹散,想起八岁那年的春天。
她贪玩,小手还不太会握笔,字也写得歪歪扭扭,非得要皇兄带着才能写出一个像样的字。
东宫的桌案于她而言过高,得坐在高凳上才能勉强够到桌面。脚底悬空,两条小腿不安分地乱晃,三心二意,字也不好好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