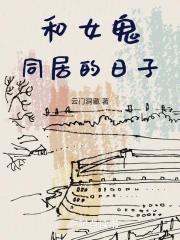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贵妃二嫁又叫什么名字 > 第38章 变故(第1页)
第38章 变故(第1页)
昭德皇后乃韩老国公和老夫人的第一个孩子,从生下来韩老国公便亲自教养,自小贤良淑德,其聪慧和胆识不输男子。
在韩家助周家平定天下后,太上皇理所当然地迎娶了她为后。
可没过几年,太上皇开始忌惮韩家,嫉妒昭德皇后的才能,逐渐对其生厌,反而日日沉迷于薛家之女的媚态之中,待二皇子一出生,太上皇对韩家的厌恶变本加厉,皇后和她所生的太子,也成了他的眼中钉。那时韩千君还小,虽然不知道宫中的情况,但能想象得到昭德皇后过得有多艰难。
尤其是太上皇几度废太子不成之后,竟生了杀心,与二皇子设计了一场阴谋,亲手将自己的儿子永远留在了战场。
韩千君依稀还记得,先太子战死的噩耗传回来后,韩家所有人都跑去了城门迎接他的灵柩,她到时,昭德皇后已立在了街头,一夜之间白了头。
六年前,她还不满四十。
从她这辈子的遭遇足以看出,男女之情,夫妻之情的确不可靠。
但辛公子不是太上皇,韩千君觉得将来自己和辛公子的生活,一定不会是昭德皇后那样的,心里想着,但不可说出来,只安静地听昭德皇后说话,点头应是。
临走时,昭德皇后给了她不少箱匣,同她道:“姑母如今给你的财富和安宁,才是这世上最难求的两样。”
韩千君知道好歹,对昭德皇后千恩万谢,“等我成亲后,再来看姑母,那时院子里的石榴熟了,我给姑母摘些进来…”
昭德皇后笑着道:“好。”
—
接下来的等待,便愈发难熬了。
郑氏知道韩千君秉性,怕她忍不住跑出去见新郎官,调了两个婢女轮番守着,韩千君只能在院子里走动,看着府上的仆妇奴才们替她忙来忙去。
离婚期还有半月,屋里到处堆放着嫁妆箱柜,几上榻上堆满了绣枕绣被绣鞋,摞了一叠又一叠。鸣春把一大摞绣帕装进漆木箱内,心头还在算计,“趁还有几日,奴婢再替娘子绣一些。”
韩千君苦笑,“我是出嫁,又不是出远门,你是打算把我一辈子的绢帕都绣好。”
鸣春笑道:“娘子做不来绣活儿,奴婢提前替娘子绣好了,到了夫家娘子就说都是自己绣的…”
绣活儿好不好,也是衡量一个小娘子的本事之一,可惜韩千君是当真握不住细细的银针,从小不是那块料,便没把时辰浪费在那上面,让她绣花,还不如罚她抄书来得痛快。
倘若她嫁的是二娘子那样的家族,郑氏或许还会按住她肩头,让她临时抱佛脚学上一二,但辛家中途被贬为了商户,家风不似旁的家族那般严苛,屋里的几个小娘子,不会针线的大有人在。
在与辛家说亲之前,郑氏便把辛家三代之内的族亲都摸了个透,全都告诉了韩千君。
辛太傅膝下只出了两个儿子,没有女儿。
辛公子乃二房二爷跟前唯一的嫡子,家中无妾室,只娶了辛夫人一人。
但大房的那位大爷是个奇葩。
当初为官之时便有一颗玲珑心,心思很重,总觉得身边的人接近他都不怀好意,这份防范不仅用在友人身上,还用在了自己的婚姻上。
一辈子没娶亲,纳回来的全是姬妾。
八个妾室,有五个妾室生都养了孩子,最大的哥儿今年已满十八了,上头还没个正式的主母。那位大爷却丝毫没觉得不妥,后宅的事情都是自己亲力亲为,实在处理不了的,便交给了二夫人,辛泽渊的母亲帮忙打理。
辛夫人怕人说闲话,怕惹上一身骚,辛二爷过世后,便不再插手大房的事,如今府上后宅里所有的事,都是由辛公子做主。
韩千君还曾感叹过,辛公子当真是能者多劳,不仅要当人先生,还早早当起了人爹。
可笑的是那辛大爷知道侄子要同国公府提亲后,比他自己成亲还着急,派人来打探韩千君的秉性,是不是个挥霍的主,一番问下来,心凉了半截,回去便找辛夫人,苦口婆心地劝说,“那可是前贵妃娘娘,咱们辛家容得下也养不起啊…”
辛夫人把人赶出去,辛大爷又去找老夫人,也没讨到好,被老夫人劈头盖脸骂了一通,骂他是守财奴,一辈子都在斤斤计较,连失去了什么都不知道…
大爷两处碰壁,只能忍气吞声自己着急,不敢再提。
如此瞧来,辛家上下除了那位大爷难对付一些,辛家倒没其他烂账。
韩千君嫁过去,会不会绣花并不紧要,自己的夫君乃一家之主,哄好了什么事不好说。
旁的没有,她哄人的本事还是有的,韩千君越想心中的思念越甚,数数日子,她已经快两个月没见到辛公子了。
正无聊,王秋怀里抱着一个漆木妆奁进来,往地上一放,额头都出了汗,禀报道:“娘子,适才门口来了一位叫韦郡的公子,说他是辛公子的学生,这个是送给娘子的新婚贺礼。”
韦郡?
韩千君一瞬起身,“他人呢?”
王秋道:“东西放下就走了……”
韩千君忙跑去门口,果然没见到人。自那夜雷雨过后,她再也没有去过私塾,韦郡能找到这里来,便是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。
韩千君又返回院子,去看那妆奁。妆奁做的很精致,外雕鸳鸯、仙鹤等鸟兽纹,共有上下三层,式样一点都不比市面上的俗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