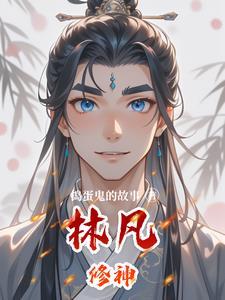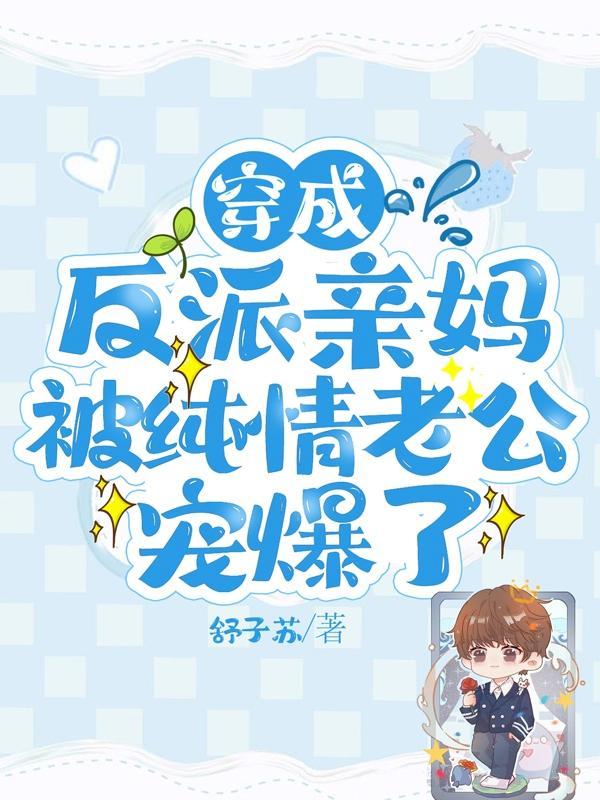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重生鉴宝完本 > 第72章 我要了(第1页)
第72章 我要了(第1页)
錾刻好花饰,接下来就是重头戏:粘和接。
这是两道工序:先在瓷瓶上涂胶,沿着裂缝涂抹均匀,半干未干之际,将树枝,也就是火柴头粗细的金片粘上去。
但只粘一半,接头处一律空开,然后自然晾干。等粘结牢固后,再焊接接头,同时焊接叶茎、树叶、叶苞。
这是个精细活,比锔瓷更为精细。因为焊药的温度高达四百度,但凡有一滴滴到瓷瓶上,“嚓”,就全炸了。
怕李贞手生,王齐志换了防护服,把她换了下来。
然后王齐志拿火枪,林思成点焊药,冯琳固定防护板。
加热、涂药、冷却……稍一凝固,林思成“噌噌”就是两刀,将多余的焊药剔除。
冯琳抽板,李贞紧随其后,涂胶,粘实。
刚开始还有些慢,主要是冯琳和李贞是第一次配合,跟不上林思成和王齐志的速度。但焊了十几处后,两个人越来越熟练。
就这样,如流水线,四个人有条不紊。
当林思成补完第一道,也是最长的一道裂缝后,商妍的瞳孔止不住的一缩。
同起,身后响起接二连三的吸气声。
釉面流转的微光里,金黄的柳枝沿着瓶底舒展。枝条纤细而柔长,新抽的叶儿泛着水意,芽苞儿将放未放,娇嫩欲滴。
明明是瓷底金枝,但恍然间,就如阳春三月一簇吐芽的柳枝,从罐底的土里长了出来,攀着梅瓶蔓延而上,越过瓶腹,拂过瓶口,又缓缓垂下。
形象,生动,自然,又充满生气。
正如之前王齐志所想像的那样,如果把柳枝染绿,谁敢说这不是从树上剪下来的?
不,甚至染都不用染,给人一种“这根柳枝,本来就应该长这样”的即视感。
下意识的,几位研究生不约而同的想起,摆在陶瓷实验室的那两只碗,和那樽腰鼓瓶。
前一只是三年前,一位读林教授博士的师兄的毕业作品。后一只是商教授亲手修复。
同样的,这两只碗都是“先锔瓷,后金缮”的修复工艺。也同样的,这两只碗都得过奖。
不同的是,师兄那只得的是协会类奖项,商教授这只则是省内省级非遗传承艺术品类最高奖项: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银奖。
只需一眼,高下立判。
但现在,如果和台上的梅瓶放在一起对比……嗯,就感觉,不管是哪一只碗,好像都没这么漂亮?
当然,也可能是碗的器型太小,以及光线的问题!
最后那一樽腰鼓瓶,则是林教授亲手修复。
也是巧,同为清中时期的民窑,同为糯米胎白釉瓷,器型同样为瓶。甚至是修补工艺都一样:先锔瓷,后錾花贴金。
唯有一点:腰鼓瓶的口非常大,林教授用的是“膛内锔”的工艺。顾名思议:锔钉在瓶膛内,从外面看不到。
同样得过奖: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,金奖。
如果和台上的梅瓶放一块对比,就感觉……嗯~~好像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生动和自然的感觉,生气也少了不少。
就好像,林教授的腰鼓瓶在冬天,林思成的梅瓶在夏天……
当然,很可能是腰鼓瓶破损的地方太少,没有足够供林教授构图、展开精妙布局的篇幅……
十来个研究生差不多都是类似的心理,但想着想着,就想不下去了:感觉,有点亏良心?
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这点鉴赏能力他们还是有的:所以怎么看,爷爷的都好像比不上孙子的?
然后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面面相觑:那是怎么回事?
总不能是,林教授教学生的时候,还留了手?
不然师兄的那只碗,对,就第一只,能补成那个逼样?
越对比,这种即视感就越强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