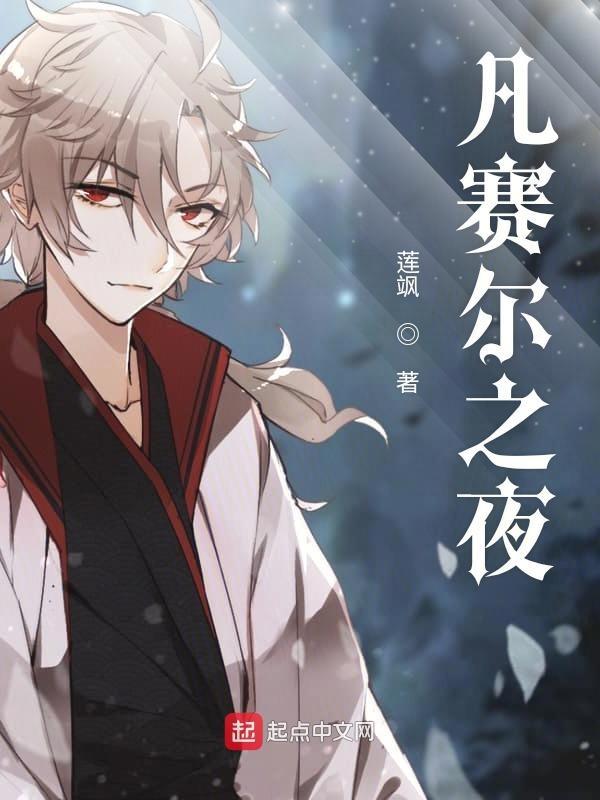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蓝色烟花为什么贵 > 第49章(第1页)
第49章(第1页)
聽出來安慰的意思瞭,宋燃輕輕嘆瞭口氣:「謝瞭耀,不過沒事」
「哎對瞭!」張耀忽然想到瞭一條關鍵的,「你活的比他久!你想啊,他現在三十多,你才二十多,你年輕身體更好,而且死的肯定比他晚」
「什麼?」宋燃被他搞笑瞭,「張耀啊張耀,你不去說相聲真是虧瞭」
北京朝陽區某別墅內。
比起宋燃的煩悶,陸江北倒顯得十分平靜。獨自坐在沙發一隅,身旁稀稀疏疏坐著幾個人,偶有人來說話,也隻是禮貌的問候,並不敢和他多說什麼。於是伴著唱片機裡的巴赫曲,他隻是靜靜坐著喝酒。
厚重的木門把手緩緩轉動,門被人推開。
張耀和宋燃隨便找瞭個地方坐下,張耀嘟囔瞭句:「怎麼放巴赫?也太老瞭。」
旁邊有人悄悄告訴他:「那個人喜歡巴赫,就有人上趕著拿瞭唱片機來放的黑膠唱片。」
宋燃擡起頭來接過侍者盤子上的酒,遞瞭杯給張耀:「那個人是誰?」
張耀擺擺手讓侍者去換歌,略有些憤憤不平道:「就是咱那個項目的祖宗。到底是有錢有權,到我的場子都有人上趕著搖尾巴。」
「他現在在哪?」
張耀四下環顧,用手指瞭指窗戶邊,「喏,那不就是。」
宋燃於是起身,徑直走瞭過去。張耀在背後喊他:「幹什麼去?!」順便拽瞭他一下,壓低聲音道:「你要幹啥?沒看見他周圍都沒人敢坐嗎?」
宋燃輕輕一掰就從張耀的手裡掙脫出來「其他人不敢是其他人的事。都是人,有什麼不敢的?」
張耀在心裡捏瞭把冷汗,「你和他也沒仇哈,就算搶人的話,也別太」話音未落,宋燃已經走到瞭窗邊。
早知道不帶他來瞭張耀心裡叫天天不應,叫地地不靈,誰知道他倆要搶同一個人啊!這也太巧瞭
宋燃拍瞭拍陸江北的肩膀:「你好,請問這裡有人嗎?」
眼裡沒有一絲波瀾,陸江北的語氣很客氣:「沒有,請坐。」
「謝謝。」宋燃坐下,把酒杯放到茶幾上。
張耀和幾個人在屏風後面緊張的觀望,張耀戳瞭戳身旁的哥們:「一會兒如果有人動手,你們幾個一塊上。」旁邊的人也很緊張,點頭大氣不敢出的緊盯對面的一舉一動。
沒有他們想象的劍拔弩張,陸江北態度很平淡,「宋燃對吧?聽蔣青提起過你。」陸江北輕輕搖晃著手裡的酒杯,藍色的酒在玻璃杯中激蕩起浪花。
沒想到上來就單刀直入主題,宋燃有些意外,但也基本快坐實瞭心裡的猜測,他點點頭:「沒錯。」
「他很久之前回瞭趟南門,在那裡當瞭一年老師,你是他的學生吧?他說你是個很聰明的學生,學東西很快,後來也考的很好。」
「是,我曾經是他的學生,但後來很快就不是瞭,現在更不是,以後也不會是。所以身份不是問題。」宋燃也不喜歡彎彎繞繞的,在打臺球時,他一般喜歡打直線球。
陸江北喝瞭一口酒,第一次擡眼平視宋燃:「老實說,你比我想的直接。」
宋燃笑瞭,不過眼神沒有因為這一絲笑意而變得溫暖,依然冷冽:「平時你應該不會參加這種場合吧?」他環顧四周,果然,「他們也不知道你今天會來,所以才會連巴赫的黑膠片都準備的這麼匆忙。陸總,你今天應該不是來喝酒唱歌的吧?」
「何以見得?」陸江北忽然來瞭點興致,眼前的人,雖然年輕幼稚,但不笨。
宋燃沒有回答他的問題,而是繼續道:「你是來見我的,對吧?」
陸江北點點頭,「不錯。」
宋燃挑瞭挑眉,「那看來我已經司馬昭之心,路人皆知瞭。」
「也不是。至少蔣青那邊,他應該還不信一個小孩的感情能堅持這麼久。」陸江北把酒杯放到桌子上,玻璃和木質的平面碰撞,發出「哐當」一聲。
隔岸觀火的張耀心髒也隨這一聲停瞭一拍,他幾乎就要沖出屏風,上去拉架瞭,但很意外,兩人仍然坐著友好交談。
「怎麼,杯子拿不穩就不要拿瞭,陸總平時也要多加鍛煉才好啊,身體才是革命的本錢。」宋燃微笑道。
「是啊,到底是年齡上來瞭,不比在多倫多那幾年,當時和朋友天天去跑步,等回國之後,過幾天再去和那個朋友一起跑步鍛煉。畢竟,有人陪著一起跑,和自己一個人早起跑,還是不太一樣。」陸江北眉毛一舒,回道。
雖然心裡已經快掀桌瞭,但宋燃臉上仍然風平浪靜,陽光燦爛,萬裡無雲:「那是自然。不過多倫多這麼好,陸總怎麼還突然回國瞭?是因為沒人陪著跑步瞭嗎?」
陸江北心裡也已經遍佈陰雲,隻是他表面也一如往常平淡:「你以為,我千裡迢迢回國花時間弄一個一二百萬的項目是為瞭什麼?」
宋燃咬瞭下嘴唇,「我不知道。但是,我知道他變瞭很多,他這些年過的不好。」
陸江北看著他的眼睛,裡面燃起經久不滅的火花,星星點點閃爍著,他忽然心裡黯然下來。
這沈默的空檔,巴赫的賦格恰到好處的響起,穿越時間的亙古不變的理性和生命的脈動間奏不絕。
「那份策劃,他看瞭嗎?」宋燃忽然問道。
「怎麼,你不自己去問嗎?」陸江北笑道,
接下來,他語氣沒變,眼裡仍是淡淡的冷漠與疏離,但陡然間與之對視靠近時,那種常年以來形成的壓迫感已然重重襲來,他開口:「他看不到。因為你的推廣策劃,我否瞭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