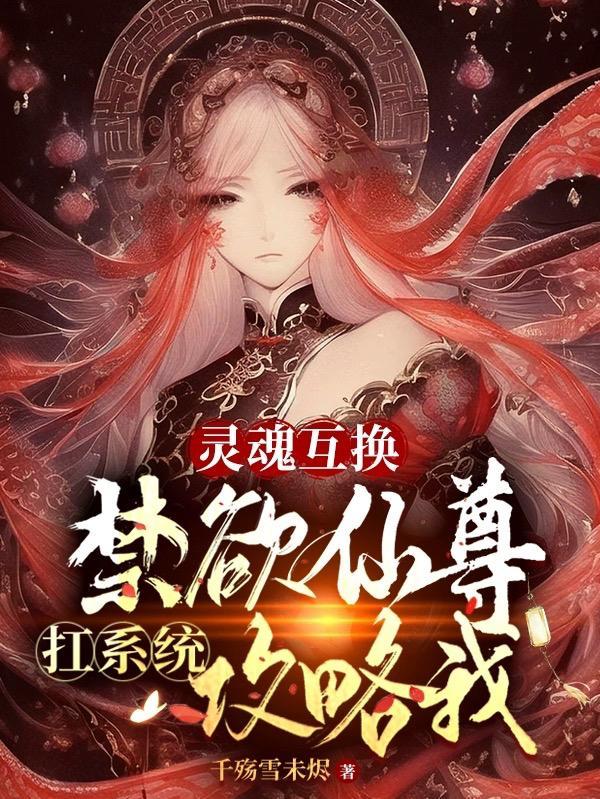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一帘风月闲茉莉不离 > 245 太医怎么说(第1页)
245 太医怎么说(第1页)
含英殿在冷清了几日之后,忽然再一次热闹了起来。
只是这一次的热闹,没有了从前的那种繁华的得意,反倒处处透着慌张和肃杀。
因为如今殿中出出进进的,不是宫里管事的嬷嬷们,而是太医院的一众太医。从王院首到太医院配药的小太监,几乎每个人都是含英殿的常客,浓郁的药气从内殿之中透出去,几乎弥漫了整座宫殿。
性情疏冷高傲的五公主一反常态地成了含英殿中的常客,连皇后也来看过几回,与含英殿主人原本便是亲如姊妹的林良娣更是日日过来请安问候,最后干脆在自己居住的疏影斋设了佛堂,日日在佛前焚香祷告。
这一切似乎都透着一股不寻常,但含英殿的宫女太监们不愧是先前照管过六宫事的,遇到这样的大事竟仍然十分镇定,虽然难掩哀戚,却还是强撑着,礼数周全地招待着每一个前来请脉换药的太医。
这一日晚间,夜寒烟照例喝下一大碗酸苦的药汁之后,忍不住艰难地皱了皱眉头。
沫儿收起药碗,恨恨地骂了一句:“自作自受,活该!”
夜寒烟想骂回去,嗓子却疼得厉害,便是用尽了力气,也只能发出一声干哑的呜咽。挫败之下,她也只能作罢。
算了,挨骂就挨骂吧,沫儿说得也没错,她是自作自受,怨不得别人。
反倒是沫儿心中不忍,拿帕子替她擦了擦嘴角流下来的药汁,忽然就忍不住掉起了金豆:“你这是何苦,再费心想想,未必没有别的法子,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凄惨……这些该死的汤药,我闻着就想吐,你却一碗一碗喝得乐此不疲!再病下去,就只剩皮包骨头了,到时候哪怕皇上来了,看到你这幅样子,你以为他还肯听你说话吗?他不掉头就走才怪呢!色衰爱弛你懂不懂?要不要我拿镜子给你照照,看看你现在是怎样一副鬼样子?”
夜寒烟想笑一下,但咧嘴似乎也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动作,她抽了抽嘴角,只得作罢。
门帘响了一下,沫儿头也没有回:“刚灌下去一碗,现在醒着呢,一时半会应该死不了,二更天的时候再看吧。”
“你们就是这么伺候主子的?”威严的声音,带着外面的寒气,骤然在殿内响起,吓得沫儿本能地打了个哆嗦,身体先于思维反应过来,“咚”地一声跪在地上,药碗摔出老远:“奴婢该死,奴婢该死。”
“你确实该死!”祁诺清重重地踹出一脚,沫儿不受控制地摔了出去,后背撞在了夜寒烟的床榻上,帷帐四角挂着的香球和银钩一阵叮叮当当乱响。
沫儿顾不上疼,忙翻身重新跪好,伏在床前不敢开口。
“还不滚出去!”祁诺清的声音很沉,听得出他在竭力压抑着愤怒,或者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情绪。沫儿不敢再迟疑,连滚带爬地沿着墙角溜了出去。
祁诺清安静地在帐外站了很久,不知道叹了多少口气,脚下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圈子,一只手抬起又放下,放下再抬起,却始终没有碰触到那一道轻软得一阵微风就能吹开的帐帘。
帐中响起一声沉闷的咳嗽,干涩喑哑,像个迟暮的老人。
祁诺清脸色一变,忘记了先前的犹疑,几乎是凭着本能一把将帐帘扯落,人已扑到枕边:“烟儿!”
首先入眼的是一片如墨的乌发,无章地铺散在淡远水墨缎面的鸳鸯枕上,几乎占去了大半个床榻,越发显得中间的那张小脸苍白得可怕。
沫儿说得没错,此时这个病重的女子,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。
祁诺清怔怔地看了很久,始终无法从这张苍白的脸上找到从前那个恣意张扬的小宫女的影子。
从含英殿传出贵妃病重的消息,到他终于忍不住前来探望,时间只过去了半个多月,可就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,一个有着明艳笑容的不到二十岁的小女人,却忽然变成了眼前这样一个气息奄奄骨瘦如柴的垂暮之人,为什么?
祁诺清的心中忽然又响起刚才那个小宫女的抱怨:
“你这是何苦……把自己弄成这幅样子……就算皇上来了……”
她在盼着他来吗?她为什么不说?
一向自以为泰山崩于前都可以从容不迫的祁诺清,忽然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。他用手紧紧地按住胸口,竭力忍住那一丝控制不住的抽痛,缓缓伸出手去,抚上那张瘦得不成样子的小脸。
冰凉。这是祁诺清能够想到的唯一一个勉强算是准确的形容。
一如他此刻的心境。
他曾经一度以为自己足够理智,为了大业的江山,他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。牺牲这个女子,虽然有些不舍,但他相信自己能够慢慢忘却;那些指向这个女子的证据,虽然荒唐可笑,他却还是假装相信,只为了给自己一个恨她、疏离她的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