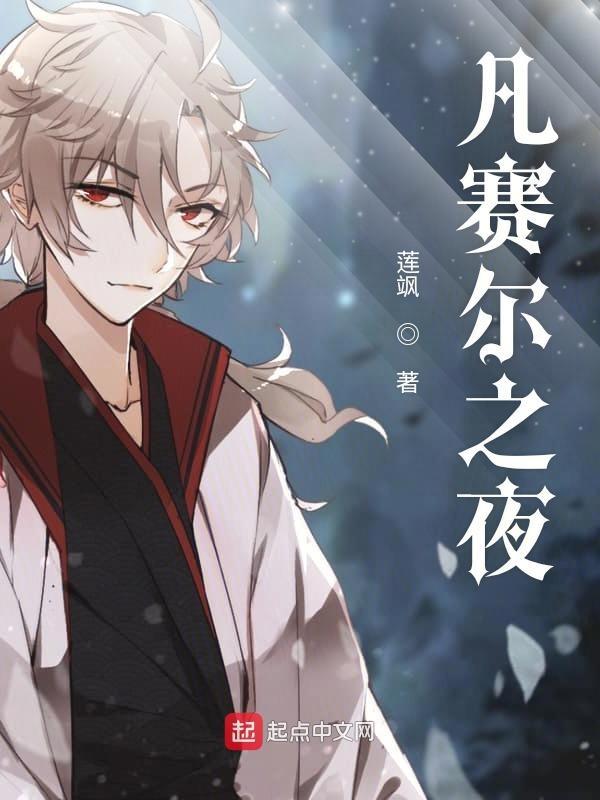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沥青路面改色漆 > 第55章(第2页)
第55章(第2页)
看着他,却叫人觉得是在透过他看另一个人。
如静置,位居高位对一切了如指掌的旁观,而他张寄置身孤巅,身后就是万丈悬崖的末路。
自己,仿佛从没真正入过宋南津的眼。
张寄试着喊了声:“……哥?”
宋南津回神,视线回拢。
“您刚刚那样看我做什么。”
宋南津扯唇,说:“没什么。”
作者有话说:
哥哥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
-
今天突然想到一个点。
或许宋南津最难受痛苦的地方不在于喜欢一个人从未得到过。
而刚好是曾经得到过。
可后来失去了。
那两天文徵工作总收到花,搁在前台落来来往往的同事眼里,初秋里的白色玫瑰、浅蓝色的满天星,大家都羡慕得紧。
问起,说文徵有个好男友,她男朋友送的。
文徵看着,人前客气回一句,回到工位丢进垃圾桶,事后,也和人说:“不算男友了。”
那天之后张寄来找过她。
解释,申辩,说自己如何苦衷,说自己是怎么鬼迷心窍。
他说他压力大。
精神压力,来自领导的压力,课业上的学习压力。他很累,他说老师是表明过那种意思,一开始是没什么,但被人恶意举报,之后,他去老师家做客老师才抱了他,他拒绝了。
他说他们的肢体接触仅这一次。
那天晚上碰面,他和老师吃饭,扪心自问,他说他确实有些混账。
他不知分寸,他心比天高,他仗着有人喜欢为所欲为,他是想图私心感受一下那种温柔。
可是。
可是。
他当时言辞极其恳切极端。
“我发誓,我对你别无二心,我心里谁也没有,没有什么老师没有什么别的女人,我的心里从头到尾彻彻底底只有文徵。”
那天就在电视台大楼底下,张寄望着她。
眼底都泛了红。
“七年,文徵,求你不看在别的,就看在我当初追着你,捧着你,把你当珍宝一样护着宠着那么久,原谅我这一次,可以吗。”
“我所有的,都可以给你。”
“我的前途,也可以给你。”
“只要你想。”
文徵当时望着眼前这个人,陌生无比。
打印机传来咔咔声,复印件出来了,她把东西从打印机上拿下来跟一封申请书别在一起,有些沉默地放在了领导的桌边。
之后收起思绪,继续回去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