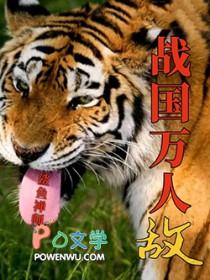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悬刀by岫青晓白 > 第100章(第1页)
第100章(第1页)
见江潜蹙起了眉,谢闻枝将新茶推至他的面前,“你自己都不清楚为何要来告诉我这些事,我虽不知有碎布一事,但他若要从此查起,恐怕其中细节微末我比你还要清楚十倍。就算这东西果真就出在他身上,姓云的也不会因此怀疑,只会觉得是同栽赃般的鬼把戏。再退而论,就算这桩案就成了冤假错案,将他藏起来也算是你我的目的之一了。”
藏起来?江潜曾经想过,若谢闻枝许可,便将陆相宜藏起来,他要报仇自有人替他报,但如今是多事之秋,不需要再有人来添乱子。
“我为何要来告诉你这些?”江潜看着谢闻枝的眼,自问道。
谢闻枝颇为无奈地抿了一口茶,他单手撑着脑袋,突然笑出了声。
“笑什麽?”江潜不解问。
“你疯了。”
“什麽?”
谢闻枝止住笑音,戏谑地看着他:“我说你疯了。我重视陆相宜,人尽皆知,无可隐瞒,但你真当我如碎云说得那般,撞见他便手足无措,举止不安,关心则乱?我看关心则乱的是你!”
喝完最后一口茶,谢闻枝起身为他推开了门:“早些将表弟送来刑部谋个差事吧,省得你再像今日般煞有介事的深夜前来,与我说这糊涂事。”
离开刑部的江潜同样忍不住笑出了声,他自嘲着,将道边石子踢进了云溶江里,赭丘漆黑一片,夜行其中只觉得滑稽,他翻过自家的高墙,另辟蹊径潜入刑部大牢,如今在同僚眼里成了一桩笑柄,他一面嘲笑着自己,一面咒骂着言栀。
从高墙翻回院中,房里头的灯还亮着,只是不见言栀其人,抄手游廊点燃了灯,一路亮到了前院。
江潜向前走了几步,见着了自家小厮,拦下来便问:“公子现在何处?”
“公子、公子在府门前坐着呢,像是来了贵客”说完话,小厮一溜烟便跑走不见蹤影。
前院,江府的大门紧闭,言栀架着腿坐在一把太师椅上,身上披着的是江潜的大氅。林随意执着火把,照着他昏昏欲睡。
江潜将手放在言栀的肩头,被手撑着的脑袋迅速擡起,言栀回眸扯出一个笑容:“回来了?”
“回来了,发生何事?”江潜正问着,便听传来一连串砸门声。
外头,许赫一身缟素,尚且在无休止地叱骂,骂的正是言栀谋害许朗,要向他讨要说法。
江潜略有愠色,正欲开口,却见言栀却笑着指了指门:“你瞧这惫赖人物,我要有他一半神气,现在就去与他打一架,直接把他扔进河里喂鱼,省得他扰我好梦。”
“大人与公子若是困了回去休息便是,府上奴仆各个忠心,这门我们替大人守!”林随意死死盯着大门,好像在等一个许赫破门而入以便他施展拳脚的契机。
江潜踱步至门前,一衆奴仆便簇拥而上,等待他的指令。
“找人去折沖府告知恭先生一声,再找几个去报官,让衙门赶紧将此人带走。”江潜冷冷道,思虑再三,还是回头走到了言栀的面前蹲了下来,道:“既然困了,就先回房睡,我一会就来陪你。”
言栀一听要他先回房,连忙打起了精神,摇头道:“你要开门,或是守着等衙门将他带走,我都要和你一起。”
江潜忍俊不禁:“这些小事”
言栀弯腰凑在他耳边喃喃:“不是你说的要并肩作战?”热气扑在江潜脸上,他再擡头时便已然对上了言栀明亮的笑容。
“好,”江潜再次来到门前,轻轻落下几个字,“开门。”
略有迟疑,林随意将火把递给下人,将门吱呀呀地打开了。
许赫见门打开,忙不叠扑向前,嘶哑咒骂:“言氏!你与我兄长比武不成,竟还要买通刺客刺杀!这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!”
林随意死死将其拦在门口,江潜肃立在言栀身旁,提高了音量:“许赫,我相府大门敞开是为劝你明辨是非,速速离去,但你若敢信口雌黄,踏入我府中半步,髒我门楣,就莫怪本相不通人情!”
许赫仍不罢休道:“言栀!兄长一生从未与人结怨,若非是你还能有谁!”
“当初的情形何人不知?那刺客来的如此之快,又怎会是我家公子!”林随意冷冷逼视道:“我家公子犯而不校,你若是再干蹬鼻子上脸,休怪我不客气!”
“呵,天子脚下,相府竟敢包庇罪魁祸首?你就不怕我报官吗!”
江潜冷笑道:“口出狂言,去取我的剑来。”
言栀一听要取剑,笑得越发开心了,他盘腿坐在太师椅上向着许赫无辜地眨了眨眼轻声做了口型:“要小心喽——”
“江潜!我乃南厉世家出生!我父亲是朝廷肱骨!你岂敢动我!”许赫怒目圆睁,视线死死咬着江潜不放,连同声音也气得颤抖起来。
在江潜的一个眼神示意后,林随意箍着许赫绕至他的身后,死死捂着他咒骂不歇的嘴,血液忽的涌上他的脸,但即使被捂着,沉闷的抗议声也同样让人头疼不已。
“大人,照胆。”小厮恭恭敬敬递上江潜的照胆,这把剑并非神兵,而是江潜自凡间取得的第一把剑,古剑已然多年未出鞘了,再次握紧如旧友般的剑鞘,江潜只觉得一股快意横生心头。
照胆在言栀的注视下出鞘,锋利的剑迎着火光挥至许赫的面前,在他眉心前凝滞住了。
“再敢多言,让你爹来为你收尸。”
江潜冷不丁的一句话如同一盆凉水倾泻而下,许赫紧紧捏住的拳头尚且在微微颤抖,但陡然浇灭怒火使他顿时陷入茫然之地,屈辱、愤怒,眼中倒映着火把暴躁的闪光,蓦然剎住愤懑地狂流,都将他死死钉在了原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