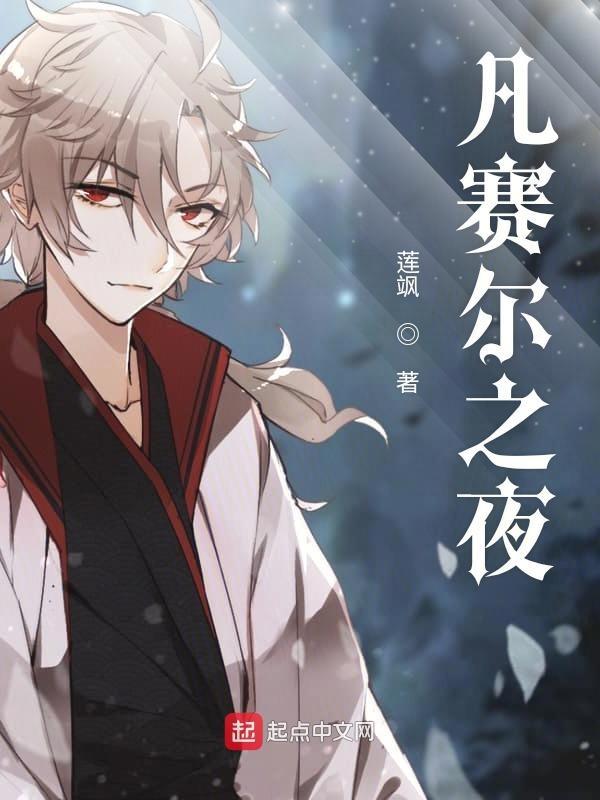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我在敌国当猫的日子by凉景生 > 第32章(第2页)
第32章(第2页)
一边的白衣公子说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商人重利而轻义,视为小人。若无法度规矩压制,任由小人泛滥,焉能长治久安。”
沉初摇头,“非也,商人重利本就是狭隘的说法,并非商人重利,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性。”
先头的圆脸公子起身说道:“圣人言:为富不仁矣;为仁不富矣。”
圣人藐视黄白之物,视钱财为粪土,引经据典商丘必然吃亏。
商屿丞幽幽开口,“这天下间最富有的莫过于各国的皇帝陛下。坐拥万裡江山,得享万民之养。”
二皇子身旁坐著的青年抬手饮尽杯中酒,豪气万千。
他说:“八年前姚州遭逢水灾,粮食颗粒无收,有商贾自粟州以七钱一斗购入粮食,运送至姚州后售价三十钱一斗,其中差价四倍有馀,姚州粮价最高时曾到四十七钱一斗。”
青年说完,立刻有人补充道:“那些坐贾行商之人肆意哄抬粮价,从中赚取暴利,以致当时姚州之中饿殍遍野。商贾眼中隻有利益,毫无道德,如此行径,和杀人凶手有何不同?”
随著他话音落下,屋中一片赞同之声。
无论是世傢出身,还是后起之秀的勋贵一脉,乃至于其他诸国,他们将商贾视为贪婪和欲望的代表。
仿佛对他们口诛笔伐,就能彰显贵族高尚的身份。
归根结底,还是“钱财”二字。
商人利用手中货物高买低卖赚取利润,积聚大量财富。
匹夫无罪,怀璧其罪。
沉初学习东丹国史时,看到过这一段,这件事记载在荣泽太子的赈灾功绩之中。
他驳道:“从粟州到姚州,中途要经过两大州府,七座城池。这一路上的关税、马匹物质的消耗、人员的雇佣,以及购买粮食的本金,所经之地分发碎米和陈米,还要防止灾民暴动,这些算下来一斗粮远远不止二十钱。商人担著风险,风餐露宿运粮到姚州,难不成还要原价售出吗?”
蓝衣青年微微提高瞭声音,“一斗米赚得十钱,十车粮食便是一位官员两年的俸禄,若是人人如此,借国难之际以谋私利,何以治国?国若不宁,钱财何用?”
言语的机锋是不见血的战场,两人对满堂十馀人。
端起碗吃饭,放下碗骂娘!
商屿丞心中冷笑。
身体向后靠著椅背,手腕打在曲起的膝盖上,看上去懒散又嚣张。
他正要开口,另一道清润的声音先他一步,“七国历一百零八年六月盛夏,大雨连绵半月有馀,各地均有不同灾情呈报,其中尤数姚州府灾情最为严重,河堤冲毁,田地房屋损毁无数,道路受阻。姚州在籍居民九万七千馀人,因灾情死亡人数五千馀衆,另有流民两万。朝廷赈灾粮款于八月末抵达,期间一个半月的粮食消耗皆由行商的商贾供应,最终姚州九万人平安度过此劫。”
他声音不疾不徐,声调甚至没有起伏,最平淡的叙述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场中那个清瘦少年身上,每个人脸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惊诧。
五皇子丹枢在他们心中就是隐形人一般的存在。
并不因此番太子案真凶浮出水面,丹枢洗清冤屈而改变,最多不过是再说起时惋惜一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