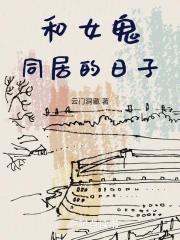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女扮男装升官指南免费阅读 > 第16章(第1页)
第16章(第1页)
李明知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他身份卑微,向来容易多想,自安蕴林出现的那一刻起就笼罩在被双方报复抛弃的恐惧之中。眼下拿到了试卷,心思一动,在临州书院课业上处处被那人压一头的阴影再度出现:安蕴林死了自己才是临州府第一,他现在回来了,自己能胜得过他吗?
不不不,现在不是在同他比对,参与会试的人这么多,名列前茅怎么都好说,千万不能被这些小事蒙蔽……不是在跟安蕴林比,不必想他、不必想他……
如此在心中默念了几遍后,李明知定了定神,开始强迫自己阅卷。
夕阳西下,一天的时间转瞬即逝。
安蕴秀聚精会神地写着答卷,四书五经的内容自然难不倒她,甚至还能借着时代和专业的优势进行拓展,推陈出新写一些前人意料之外的答案。直至光线渐渐暗了下来,她这才放下笔,揉了揉手腕。
号舍里充斥着一股异味,她虽然拿布巾蒙着口鼻,努力忽视这些外物,可有影响就是有影响。一天下来,臭味的刺激已经不如刚进来时那样明显,可她却觉得自己浑身都沾染了这股子气味,想想还挺不舒服的。
不对。
安蕴秀眉头一皱,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
她取下蒙面的布巾,偏头闻了闻自己的衣裳,随即又拿起已经作答完毕的试卷凑到鼻尖闻。眼下墨迹已干,鼻翼间萦绕着的合该是纸墨香气,可她居然不太能分辨了,似乎是因为在这污浊的环境中待久了、熏透了,所有物什都沾染上这污浊的气味,融为一体难以分辨。
安蕴秀的神色渐渐冷了下去。
原以为臭号只是在过程中折磨自己,没成想还能在试卷上留下气味标记,自己这答卷被拿出去后定然十分明显,届时阅卷队伍中若有洪家的人,让自己名落孙山可以说是轻而易举。
虽说这事猜得不一定准,抽到臭号的也并非自己一人,可安蕴秀不敢掉以轻心,趁着休息的功夫立刻四下查看起来,不多时,目光便盯上了角落里的一堆枯枝木柴。
号舍里是可以做饭的,眼下便有羹饭气息传来,只不过自己带的是干粮,用不上这些柴火。安蕴秀心下已有主意,上前挑拣了几根大小合适的枝干放在角落里点燃,左右现在正是生火做饭的点儿,也不怕引人怀疑。
她小心地控制着火势,待木柴烧得通红时便一瓢冷水浇下去,登时嗞嗞之声不绝于耳。等青烟散去,她另寻了一根树枝扒拉着面前这黑乎乎的东西,寻了好久,终于扒拉出了几块碎木炭。
木炭的吸附性不错,惯常是当作除臭剂的,应当能将气味消个七七八八。再不济,生火做饭的考生那么多,任谁都会沾上些微木柴炭火味,如出一辙的气味足够迷惑对方。
安蕴秀拿遮面的布巾将木炭包住,并将之与试卷放在一起,又另寻了件衣服小心翼翼地将试卷和木炭包了个严实,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她宁愿是自己想多了,也不敢放过分毫可能的错漏。
此后便如法炮制,每张试卷都要这样仔仔细细做一遍,直到清晰地闻到木炭的气味才放下心来,前面几场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。
到第三场时,众人紧绷了几日神经难免疲惫,又因愈发接近结束时间而紧张,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严肃的气息。安蕴秀攥了攥手指,也感到有些挑战。
这第三场,考的是策论。
之前那些经义要闻自己虽然能应付,但放在寒窗苦读的举人们中间,想要一枝独秀也是极为艰难的。第三场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事,她知道这才是分出高下的地方。
这场策论,问的是关于税收。
安蕴秀看到题目时便松了口气,暗道自己这是走运了,不必再用那套西红柿炒蛋理论。
税收向来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,这个大晋朝虽是架空的,但想来历史发展轨迹也有相似之处,税收方式多为田税和人头税。只不过长久发展下来多有弊病,早就到了该变革的时候,近些年一直有朝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。而对于这个问题,一条鞭法无疑是一剂良方。
当初在临州,她被徐莽一句人头税点醒,当时就萌生了这个想法,如今倒是能光明正大地写出来了。即便日后被问及此策,在临州的所见所闻足以成为理由,也足够给徐知府摆一道。
思及此,安蕴秀不再犹豫,斟酌了下用词就开始落笔。这次不必什么华丽辞藻,只需质朴务实,加上自己前世的专业加持,复述一遍早已烂熟于心的东西自然不是什么难事。
号舍之中,时间悄然而逝。安蕴秀花了两天才将策论写好,随即用木炭除臭,收拾好一切后就躺下闭目养神,静静地等着贡院钟响。心里则盘算着先前搜身之事发酵的情况,也不知胡曜有没有去与洪家对峙,会不会用得着自己。
不过即便没有这事,自己也少不得与徐开荣李明知打交道。她翻了个身,心道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得好。
待到贡院钟响的时候,安蕴秀猛地睁开眼睛,眸中一片清明。
她目前精神正好,该去迎接下一场挑战了。
新朋旧友
出贡院时显然没有进来时热闹,众人经历了这九天的摧残,大多都是蔫了吧唧的。安蕴秀精神尚可,只不过身上的味道不敢恭维,似乎还有之前当众辩论的威慑,一路走来,身边的人皆是退避三舍。
她并不在意,如此这般正阔步往前走着,忽然有个人停在面前挡住了去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