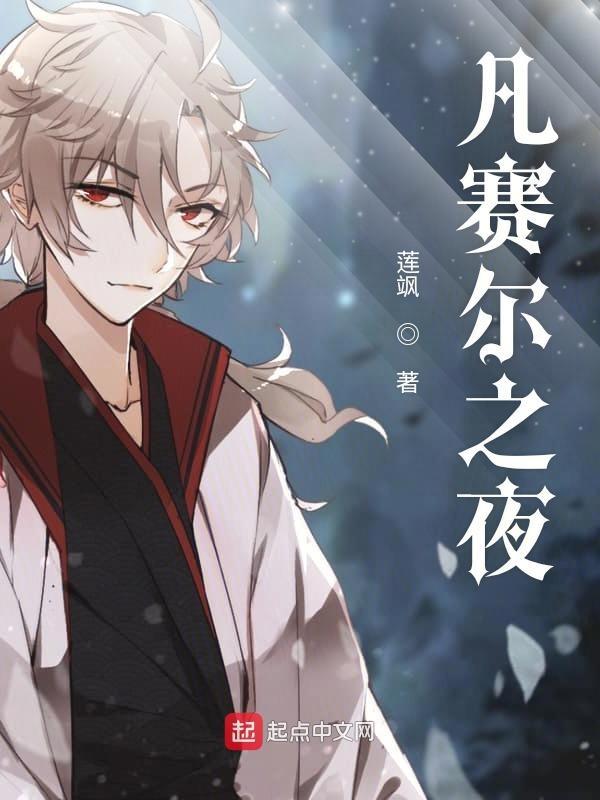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羽尖的轨迹 > 第38章(第1页)
第38章(第1页)
“哥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重操旧业,也没有强制你不让你画的意思,只是你现在已经高二了,要分得清轻重缓急。”谢子晟的语气并不强硬,却足够不可动摇。他看着谢子夕的眼神温柔又坚定,无形之中就让谢子夕没有底气反驳,“以前还让你画是因为那时候竞争没那么激烈,现在你应该看得清局势了。”
谢子夕动了动嘴唇,最终还是放弃了挣扎,转身向楼道里走去:“我知道。回去吧。”
岑林给岑穆一连打了几个电话,那边都没有回音,他心头一紧,一边安慰自己爷爷可能是没带手机,一边撒腿跑到路口直接叫出租车。
即便他清楚爷爷即便上了年纪,记性也不差,从来不会忘记带手机,更别说那么多电话没一个打通的。
那天晚上他的预感第一次灵验,等他挂掉不知道第几个电话,他已经站在了鹿角巷小院门口。
没过多久,救护车驶进了鹿角巷,接走了岑穆。
……
突然,谢子夕房间里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,夹杂着一声闷哼,岑林思绪被打断,下意识快速站了起来往谢子夕房间走去:“怎么了?”
里面没有声音,只有木耳的尖叫声和它抓挠房门的声音——谢子夕的房间习惯上锁。
岑林刚想起岑穆那时候悄无声息就到来的疾病,联想到谢子夕从那时候起就已经废掉的胃,手指开始微微颤抖。
这种时候,什么应该记一辈子的梁子,什么这人就是满嘴谎话,他通通都不管了,反正事后他也只是说自己是ptsd犯了,却在当下毫不犹豫地想要靠蛮力把门砸开。
他都已经进了厨房把菜刀拿上了,刚准备砍,伴随着木耳的一声尖锐的叫,门开了,然后岑林看见了谢子夕那张惨白的脸。
谢子夕一手在长款针织衫外套下捂着胃,鬓角还有一点未擦干净的冷汗,微微皱着眉。当看见岑林手上举着的菜刀时,她明显愣了一下,抿了抿唇:“你这是要干什么,终于忍受不了我要谋杀我了吗?”
她似乎还没缓过来,声音气息不足,面上看着十分镇定,可是光听声音,这人就像快要不行了。
岑林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菜刀,按照谢子夕的说法,自己确实有点像要行凶的,赶紧放下了刀:“我……我听见你这儿有动静,你又不开门,我以为……”
“我无论如何都死不了的,祸害遗千年嘛。”谢子夕把腰挺直了些,好让自己瞧着精神点。木耳又绕回来蹲在她脚边拿脑袋蹭她,一声接一声地叫。
谢子夕低头看了看它,无奈地叹了口气:“我还没死呢,它这是忙着给谁哀悼?”
岑林回厨房放下菜刀,闻言回头上下打量她一眼,瞅见她藏在外衣下的手,又看看她跟死人一样的脸色,冷哼一声:“别装了好吗,你在我面前能藏得住什么。”
谢子夕充耳不闻,好像岑林说的不是她一样,径自站在那里,只是眼睛往客厅看。
岑林想起她之前回来的时候好像是把胃药放在客厅了,他还记得放的位置,看着谢子夕死要面子实在难受,赶在谢子夕反应过来之前先一步打开抽屉把药拿了过来:“你这个人,难受就难受,干嘛非得跟自己过不去?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你这样的了。”
谢子夕看着岑林拿过来的药,一时间不知道该接还是不该接,眼看着岑林脸上逐渐露出不耐烦的神色,她才一把薅过转身去倒水。
岑林从谢子夕站在灯光下吃药的背影移开目光。现在已经三点多了,距离谢子夕回来也有好一会了,他应该是又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最近一段时间他老是想起以前的事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回到了云城的原因。
谢子夕咽了热水,胃还是疼,现在挺直腰杆都做不到了。她深呼吸几口气,最终还是弯下了腰。
岑林见状立刻走了过来,伸出手想扶她一把:“你没事吧……”
他还没说完,就见谢子夕一只手撑住流理台,颤抖着喘了几口气,慢慢抬起头:“用不着,吃了药就好,反正又死不了。”
那一瞬间,岑林好像又看见了那天晚上的谢子夕,什么都不怕,唯一能绊住她脚步的似乎只有谢子晟。那个时候她连死都不放在眼里,或者说,她根本没把自己的命当回事。
后来他们在一起了,也没见谢子夕有多收敛,还是那么天不怕地不怕,别人都说一旦喜欢上了一个人,既有了盔甲也有了软肋,到了谢子夕这里仿佛就只给她加了盔甲。岑林是真的喜欢她,可她从来没让岑林有过被依赖的感觉。他知道谢子夕这是习惯了所有事情自己解决,然而这种不平衡有的时候会让他有一种挫败感,就好像他没有足够的能力能让谢子夕完全信任他、完全把自己交给他。
七年了,她还是这样,什么都不用他插手,无论自己有多难受、无论事情有多棘手,找他帮忙从来都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。
他突然就感到一阵迟来的愤怒,这愤怒本该在重遇谢子夕的第一天就出现,可是直到今天,岑林才明白,这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人、什么事能改变这个人。她依然是谁都不想靠,谁都不想信,至少不信他,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牵绊,他都不是谢子夕会求助的那个人。那些愤怒剎那间就铺天盖地地压过来了,还夹杂了些别的说不清的东西。
他快速上前一步,把谢子夕打横抱起丢在了她房间的床上:“身体不舒服服个软能掉块肉吗,你到底在坚持些什么?非要等自己死了才后悔没提前找个人给你安排后事是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