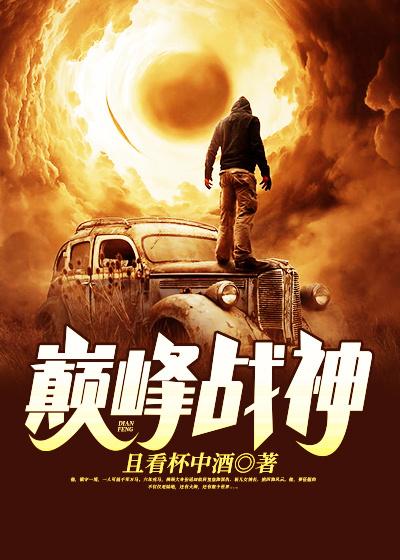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一品狂兵 > 第14章 安抚丫鬟巡视庄田(第2页)
第14章 安抚丫鬟巡视庄田(第2页)
“我去庄子上转转,亲眼看看情况。”
“顺便,也该让乡亲们知道,方家还没倒,我这个少爷,还在。”
他拍了拍秋月的肩膀,语气带着鼓励。
“你继续看着火,记住我教你的要点,别让它灭了,也别烧得太旺,注意安全。”
“有任何不对劲,或者酒快接满了,就大声喊我。”
“嗯!少爷放心去吧!这里有我呢!”
秋月挺起小胸脯,一脸认真地保证道。
方寒这才迈开步子,朝着祖宅后面,庄户们聚居的方向走去。
方家的庄子,其实就在祖宅后面不远处的一片坡地上。
十几户人家,稀稀拉拉地散布着。
房屋大多是夯土为墙,茅草盖顶,显得低矮而破败,在清晨的微光下透着一股子萧瑟。
田地看起来也并不肥沃,土色泛黄,零星散落着一些顽强的野草。
方寒一路慢慢走过去,脚步不快。
田埂上,零星有几个早起的庄户正在劳作。
远远看见他的身影,都纷纷停下手里的活计。
男人们慌忙脱下头上的破草帽,远远地就躬下身子,头颅低垂,不敢直视。
妇人们则赶紧拉着身边衣衫褴褛的孩子,悄无声息地退到路边,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打量。
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厚的、属于乡野的味道,是泥土的腥气、牲口粪便的臭气,还有陈年茅草腐烂的气息混合在一起。
这就是他现在拥有的基本盘。
一群贫穷、卑微、麻木,却又与他命运紧密相连的人。
方寒没有摆出任何高高在上的少爷架子,只是平静地走着,目光沉静地扫过这片贫瘠的土地,和土地上那些同样贫瘠的人。
他的目光落在一个正在费力锄地的老农身上。
头发花白,背脊佝偻得几乎要折断,身上的粗布短褂补丁摞着补丁,颜色都已混沌不清。
他走了过去。
那老农像是受惊的兔子,猛地一颤,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差点脱手,扔下农具,双膝一软,就要直挺挺地跪下去。
“老人家,不必多礼。”
方寒及时伸手虚扶了一把,阻止了他这刻在骨子里的动作。
他的声音,刻意放得平和,不带丝毫上位者的压迫。
老农战战兢兢地站直了些,头却埋得更低,那双布满老茧、指甲缝里全是黑泥的手,紧张地在身前无措地搓着,根本不敢抬头看方寒一眼。
“老人家贵姓?在这庄子上多少年头了?”
方寒的语气温和得像是在闲话家常。
老农浑浊的眼睛里,瞬间闪过一丝受宠若惊的慌乱,嘴唇哆嗦着,结结巴巴地回话。
“回…回少爷…小老儿…姓…姓田…打…打记事起…就在这儿了…”
“最近庄子里还算太平?”
“太平…太平着呢…”
“地里的收成如何?家里人都能吃饱肚子么?”
方寒问得很细致,目光平静,带着一种纯粹的关切,没有半点审视的意味。
田老汉被问得有些发懵。
少爷今天是怎么了?怎么关心起他们这些泥腿子的吃食来了?
他愣愣地,飞快地抬眼皮瞥了方寒一眼,触及对方平静的目光,又像被针扎了似的,赶紧低下头。
“托…托少爷的福…还…还过得去…”
声音干涩嘶哑,是长年累月风吹日晒和辛劳留下的印记。
方寒又和旁边几个闻声凑过来,却又畏畏缩缩不敢靠近的庄户聊了几句。
问的也都是些家长里短,年景收成,家里几口人丁,半大的小子多大了。
他没有端任何架子。
甚至还尝试着,就着阴晴不定的天气,说了句半带玩笑的话。
庄户们先是齐齐一愣,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,像是没听懂。
过了好一会儿,才有人反应过来,咧开嘴,露出一口黄牙,脸上是憨厚中带着十二分拘谨和惶恐的笑容。
气氛,似乎因此而缓和了那么一丝丝。
但那份世代相传、深入骨髓的敬畏,依旧像一道无形的厚墙,横亘在他们与方寒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