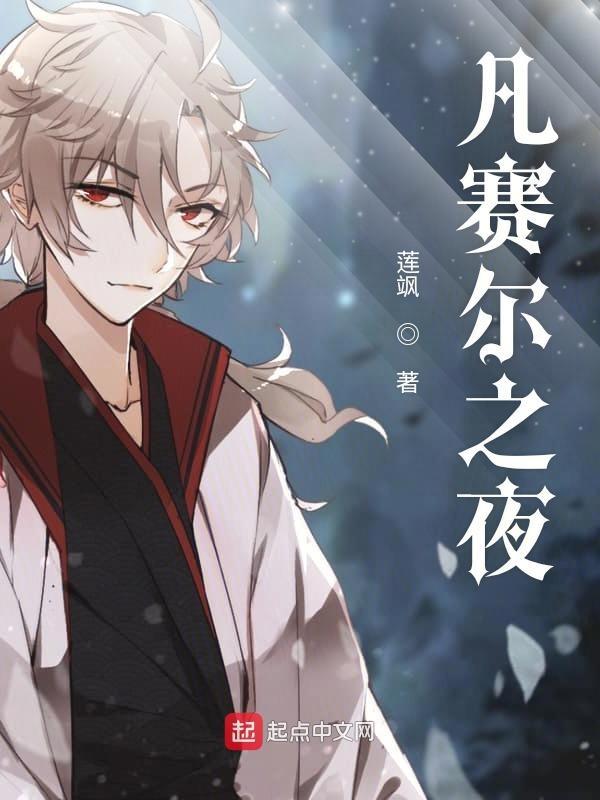日照小说>鱼目混珠成语图片 > 第103章(第1页)
第103章(第1页)
此时已近日暮,傅至景一天都耗在了这里,听老夫妇讲诉这五年来有关孟渔的点点滴滴,只嫌时辰走得太快,无法知悉完整。
他感怀老夫妇对孟渔的救命之恩,也深谢村民对孟渔的照顾,一番思虑下来,出手很是阔绰。
赏老夫妇黄金五十两,命布政使为其翻新旧屋,从镇上买两个奴仆日后供二人差遣,其次,凡是渔村的村民皆免十年海税田税,赏文钱五贯,此外,在村庄里建立私塾,让村民的子孙都有书可读,延益百年。
小渔村被天大的好事砸中,纷纷猜测起孟渔的身份,莫不是哪个流落民间的王孙贵族,幸而素日众人都对他疼爱有加,不曾有过半点苛待,否则要是问起罪来那可怎么办是好?
老夫妇穷苦了一辈子,摇身一变竟成了方圆百里数一数二的富户,村民闻言都前来贺喜,夸他们好心有好报,小鱼是天大的福星。
小鱼被他们围了起来,众人一口一个“往后要去过好日子了,千万别忘了村里的大伙儿”、“得了空就回来看看”,七嘴八舌地恭喜他。
他懵懵地张着眼,听不太懂的样子,半天才嗫嚅道:“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何大娘和王大叔也没料到小鱼来路不凡,但他们是真心盼着小鱼好,京都来的傅大人金相玉振、气宇轩昂,且在他口中小鱼与他是青梅竹马,二人年少定情,若非小鱼不知踪迹,早已是璧人一双。
二老年岁渐长,没有心力再照顾小鱼,小鱼能去过富贵日子总比和他们待在这穷乡僻壤要强,因而尽管极为不舍,他们仍是应承傅至景带走小鱼的请求。
一切都打点妥当,小鱼却不肯走,红着眼睛问何大娘,“你不要我了吗?”
何大娘心疼得不得了,连连摆手,可无论她如何劝说,小鱼就是躲在茅草屋里不肯出去,她怕贵人等得不耐烦,急得团团转。
小鱼脱了鞋三两下钻进鸳鸯被里,露出两只圆圆的眼睛,还是那句话,“我哪里也不去。”
傅至景走了进来,小鱼见着他,把整张脸都蒙住,身形彻底看不见了。
“何大娘,小鱼舍不得你情有可原,我今夜在此借宿一晚,和他谈谈心,明日天亮再走。”
这儿是林家给林明环和小鱼布置的婚房,让傅至景住了算什么道理,可何大娘瞥了眼屋外人高马大的衙差,再看一眼神采英拔的傅至景,没敢出言反对。
福广接了食盒放在桌上,在屋里加了几盏蜡烛,挑高了灯芯,“奴才到门外守夜。”
傅至景颔首,等门关严实了,仔细地打量起简陋的小屋,红烛暖帐,喜气洋洋,正对着门的墙上贴着两张写了喜字的红纸,一看就是孟渔的手笔,他起身将碍眼的红纸撕下来丢在了墙角。
孟渔还躲在被窝里不肯见他,他打开食盒,端了一盆奶酥靠近床榻。
一张闷得红扑扑的脸蛋从鸳鸯被里探了出来,气鼓鼓地望着他,警告道:“你不许过来。”
傅至景当真如他所言停在两步之外的地方,晃了晃手上的瓷盘,“我只想给你拿些吃的。”
小鱼的肚子很不恰当地咕咕响两声。
傅至景垂眸低笑,慢慢靠近了将瓷盘放在榻沿。
小鱼没吃过这么精致的点心,在傅至景的示意下抓了一块奶酥往嘴里送,浓郁的奶香味顿时充斥着整个口腔,本该是可口的糕点,不知为何,这味道却莫名使得他胃里一阵恶心。
傅至景正想等孟渔露出熟稔的令他牵挂的陶然神情,岂知下一刻孟渔竟翻身下床,将吃进去的奶酥呸呸吐了出来,榻沿的奶酥也被碰倒掉了一地。
小鱼把奶酥吐干净,表达自己的不满,“难吃,我不喜欢。”
他还穿着火红修身的喜服,头发有点儿乱,一张脸在烛火里泛着明媚的光,眼里对奶酥的厌恶真真实实地流露出来。
傅至景的心一下子乱了。
尽管孟渔记不得他,却在本能地排斥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,以前轻而易举能哄他高兴的奶酥此时也变成了难以下咽的糟糠。
小鱼又想躲回榻上,被傅至景抓住了手腕。
他不留余力地挣扎起来,觉得这人好无礼,动不动就碰他,不仅无礼,还是个欺负明环的混蛋。
明环对他那么好,给他买酱肘子吃、替他抓萤火虫,还给他编蚂蚱灯,欺负明环就是欺负他。
小鱼瞪着眼,张嘴要咬傅至景抓着他的手,傅至景躲了下,他爬到榻上,见对方还想来抓他,气道:“这是明环和我的床,你不准上来。”
不准这两个字用在傅至景身上简直荒诞。
他站在榻旁,看还穿着喜服的孟渔像捍卫配偶领地般抱着成婚用的鸳鸯被,张牙舞爪企图吓退入侵者,心里的不悦一瞬间堆到了顶峰。
如果不是他追忆往昔前往川西,又心血来潮绕路监看正在搭建的灯塔,他不会路过小渔村,也见不到尚在人间的孟渔,对方会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和另外一个男子结契,幸福美满地过一生——偏偏连天都站在他这边,要他赶在最后一刻改写结局,与孟渔再续前缘。
小鱼只见傅至景的眉眼越来越冷,天生对于危险的警觉让他想逃,可惜才刚有动作就被对方察觉。
傅至景伸手去解孟渔的喜服,孟渔被吓呆了,懵了一下才知道叫。
门外的福广听见叫声,暗道不好,难道新帝要霸王硬上弓?
布政使和他尴尬地对视一眼,当作什么都没听到,这回真是助纣为虐了。
喜服被丢到地上,傅至景褪靴上榻,用双臂将只穿着一层洁白单衣的孟渔禁锢在怀里,轻揉抖抖瑟瑟的身躯,安抚道:“别动,我不做别的。”